“思兰德”大健康项目案背后的产业困局
2025-02-13 03:55:02
滕县保卫战川军伤亡殆尽,汤恩伯见死不救,竟有人称其“真英雄”
最近在查川军滕县保卫战资料时看到一篇文章《台儿庄大捷真相:汤恩伯真英雄!李宗仁昏馈误国!》(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搜索标题查看原文)不禁大吃一惊,这大大颠覆以往的观点。

笔者仔细拜读了文章,发现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李宗仁的回忆录。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提到台儿庄大战时,在战役最关键时刻,他多次催促汤恩伯军团出击,但汤却“逡巡不前”。最后李宗仁威胁再不出动要照韩复榘前例处置。
《台》文认为是李宗仁甩锅给汤恩伯,抹黑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才是逆转台儿庄战局的最大功臣,是“真英雄”,而李宗仁昏聩,频出乱招,差点导致台儿庄战役失败。
这篇文章很长,写了临沂战役,滕县保卫战,台儿庄保卫战。前面两场战事主要描述李宗仁的战术错误,最后那场主要描叙汤恩伯的功绩。限于篇幅原因,我们今天先谈川军的滕县保卫战,其他两部分有时间再一一拆解。
上述文章认为川军死守滕县遭受重大损失,122师师长王铭章牺牲,是李宗仁错误指挥造成,并非汤恩伯见死不救。其依据有两点:
1、李宗仁从未命令汤军团主力直接救援滕县,而是要其迂回邹县,与川军第22集团军夹击日军。
2、汤军团和川军无法完成上述命令,而且汤接到第二个命令的16日,滕县已经沦陷(事实王铭章17日才牺牲,18日仍有零星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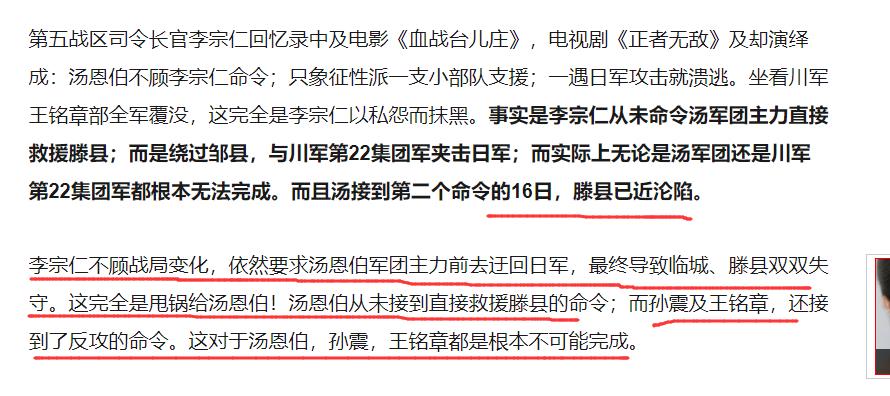
先简单介绍一下汤恩伯军团参加台儿庄大战的背景,韩复榘不战而放弃济南后,津浦路北段门户洞开。日军计划分两路南下台儿庄,而滕县正是台儿庄北方的屏障。当时川军22集团军刚从山西调过来,他们装备本来就很差,又在娘子关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因此五战区兵力是不足的。
李宗仁向老蒋求援,得到允许调汤恩伯第20军团和孙连仲第2集团军参战。李宗仁最初的部署是以孙集团布防台儿庄正面战场,汤军团以一部增援滕县,以主力侧击日军。
李宗仁是否下令汤恩伯军团救援滕县?显然是有的,《台》文中都提到李宗仁3月14日电汤恩伯“调贵军团八五军驻商丘之一整师,由火车输送至滕县附近,作二十二集团之总预备队。”
预备队是什么意思?就是调给川军指挥,必要的时候可以补防线,可以掩护主力撤退,也可以作为生力军发动反击。至于怎么用,那要由前线指挥官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作为战区最高指挥官不可能事无巨细全安排妥当,但汤恩伯的增援部队任务是很明确的,就是协助川军。
不过,汤恩伯对此方案是不同意的,在接到李宗仁电文后,他立刻致电老蒋想要推翻李宗仁的命令。电文中说:
似此分割使用,非特力量分散,于指挥上亦感困难。职意如有向该方增援之必要,可用本军团全力,向该方出击。若以零碎补孔,不但于战局无益,力量无代价之消耗,殊属可惜。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电文中明明每个字都认识,但你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认真揣摩发电人的心理,是很难理解发电人的真实用意的。汤恩伯基本意思就是不想把自己的部队分散给别人指挥。
汤恩伯
一师一师地调入战区配合其他部队作战,肯定是要给别的指挥官指挥。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军人往往把部队当成自己的私人财产。每当遇到战事时,不是自己嫡系的部队,往往被分散使用,拿去补窟窿。
比如淞沪会战,滇军到一师上一师,桂军到一师上一师,就连全副美械的税警团一下车就被中央军分散拉去补充部队了,这些部队有的打一两天就全没了。这就好像一辆豪车,自己舍不得开,你却要借去跑机耕路,车主当然不愿意,这就是汤恩伯的真实心态。
但是,别的部队分散使用的时候往往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汤恩伯有。他的电文得到了老蒋的批准,所以从一开始汤恩伯就没打算听李宗仁的。李宗仁明明命令他先派一师增援滕县,但他坚持全军团出动,集结好后再出击。火烧眉毛啊,等你集结好,黄花菜都凉了。
李宗仁不仅下令汤恩伯增援滕县,而且多次下令。当然,如今公开的史料只是历史冰山的一角,当时的档案或电话我们不可能全部获知,我们仅从能够查阅到的资料分析。
3月15日这天日军已经对滕县发起进攻,李宗仁于上午10时电老蒋:“令王(仲廉)军先行之第四师以先头之一部开往滕县以增强之。”汤恩伯收到命令后报告老蒋:“职奉李司令长官命令,本晚派一团控置于滕县以南山地,巩固22集团右侧背之安全,第四师、八十九师主力,拟集结临城东北地区,待机出击。”
到这里,命令被打了个折扣,原本要求一个师增援现在变成一个团了。不仅兵力打了折扣,行动目的也打了折扣。李宗仁的命令是要该军在滕县以南集结增援滕县,汤恩伯是怎么向下级下令的呢?来看看王仲廉的回忆:
3月14日午,余奉汤军团长特颁下因滕县告急,令本军(八十五军)驰援,限于3月16日向滕县以南之临城地区集结。
临城就是今天的枣庄薛城区,距离滕县40多公里,在这么远的地方集结如何增强滕县的守卫?当时可没有能打40公里远的火炮。其实,汤恩伯的用意已经表露无遗了,他是要让先头部队掩护主力集结,而不是去增援滕县。
日军攻占滕县
不过,汤恩伯对此还不放心,又于15日上午8时打电话给王仲廉,说我已经到徐州了,你过来一会。当天,两人在中国银行大楼上会面,共进晚餐。汤恩伯告诉王仲廉,日军已经突破川军多处防线,并沿铁路正面南下,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滕县以南之南沙河(距离滕县10公里)。所以,咱们想在滕县与日军决战的计划必须更改,因为89师还未集结完毕。
王仲廉认为应该:“调267旅占领官桥,扼守铁路正面,掩护主力,迅速集中,以求在临城附近与敌决战。”也就是说到此,汤恩伯军团彻底放弃救援滕县、侧击日军计划,而是擅自改为在临城与日军决战。
但前线川军还蒙在鼓里,3月16日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时,22集团军向李宗仁求援,电文中说:“恳飞饬汤军团部队沿滕城东南门出击,俾临、滕交通不致中断。”李宗仁于当日17时将该电文转发给老蒋,并加上:“刻八十五军之第四师已到临城下车,八十九师正向临城运送中,五十二军将续开韩庄。”
言外之意就是,汤军团先头部队到了,但没增援,让老蒋自己下令。因为大家都是同仁,抬头不见低头见,李宗仁不好在老蒋面前说汤恩伯的坏话,那样有失格局,只能委婉地表达。
老蒋大概在这时给汤恩伯下了命令,所以汤恩伯在3月17日的电文中以承诺的口吻说:“请令孙副总司令震饬令该守城部队努力支持该城至十八日拂晓,伊负责解围。本十七日先以一团支援守城。”
川军王铭章师长在守城之前就与部下商量这点兵力最多只能守一天,结果到17日他们已经守了三天了。而且这一天日军增援部队到达,以重火力轰击滕县,连城墙都被炸平了。汤恩伯先头部队15日就到前线,却仍要说你们再守一天,我18日解围。
汤恩伯还向老蒋吹了个牛,说18日决定亲率两师迂回滕县南北。事实上,当天下午王铭章在滕县阵亡,川军余部与日军进行巷战直到18日中午,仅有少数部队突围出城。始终未见汤恩伯一兵一卒。
滕县陷落,汤恩伯有了不出击的理由,但这也对他前一天的吹牛打脸,这时他怎么向老蒋解释?在18日的电文中他说:“22集团军前方已无一兵,职为考虑徐州并为部队集中,不得不先巩固正面。”
综上所述,李宗仁不仅给汤恩伯下令了,而且从公开的资料中就可以找到很多次。
王铭章
二、汤恩伯军团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一开始就分析了,汤恩伯并不愿意给别人打下手,他一开始就想在临城集结主力与日军决战,建立功勋。但架不住老蒋的命令,只能搞变通象征性地向南沙河派出少部分兵力。
根据往来电文可以得知,汤军团先头部队15日到达临城,这一天日军尚未迂回到滕县以南,如果汤有心增援,完全可以提前占领阵地。这一天下午,川军一个团奉命回援,途中两次遭日军阻击,仍有一个营于17时赶到城内。所以,汤恩伯要增援也是可以实现的。
但汤军团267旅16日才开始向滕县出发,正好在南沙河一带与日军的迂回部队遭遇,被击溃。此时,汤恩伯发现日军重兵赶过来,并且有向枣庄进攻的征兆,更加不敢增援滕县了。而是下令部队占领阵地,掩护主力集结。
根据日军方面的史料,日军第63联队第三大队于12点20分左右在一个无名村落突破了百余人的防守后集中火力袭击了“向北移动之敌,数量约5-600名”“并命令右第一线第九中队对残敌发起急追,敌周章狼狈遗弃器材装具向西南及西方溃逃”。日军于13时35分占领南沙河。
这一点与孙震事后写的战斗详报相吻合:“惟是日(16日)午,汤军第四师有抵官桥及临城东北高城一线,而敌之一部亦于此时到达滕县南之南沙河。我铁甲车曾分队力战拒止,以待友军到达,不幸车头被毁,南沙河为敌占领。”
也就是说,汤恩伯派出少量部队向滕县方向移动,与日军战斗不到一小时后就“遗弃器材装具而逃”。自此之后,汤部再也没有向滕县增援的举动。
那么,汤恩伯掩护主力在临城集结与日军决战的战略意图实现了吗?
17日,滕县被攻破后,日军便调主力南线准备进攻临城。至15点20分左右,日军已经攻破临城外围据点,抵达距离临城3公里处的黄店。日军用了30分钟攻破黄店,继续追击到达西仓桥时发现汤恩伯部已经撤离。
被日军缴获的铁甲列车
至下午17时左右日军完全占领临城,汤恩伯部不战而退。在此前后滕县的王铭章师长殉国,其余部仍在与日军巷战,直至18日才突围而出。汤恩伯预定进行决战的地点竟然比滕县更先陷落。
对此,汤恩伯是怎么解释的?汤恩伯的战报中说:
我八十五军之第八十九师昨17日逐次到达陆续应战,敌节节进逼,四面突窜,该师步步为营,随地血战,至晚阵地错杂,态势欠佳,乃以之乘夜转移于临城东南数公里之井家峪、东鉅山占领阵地。第四师原以稳固滕县右侧背,奉命以一部挺进龙山、虎山,既以滕县友军覆没,城陷敌手,该项挺进部队,虽连日作战,甚为得手,惟以滕县、官桥均失,陷于孤立绝援,故以该师课予阻敌东窜及与第89师掎角鼎立互为援之任务,遂移于山口、枣庄、卧虎寨、李山口一线,占领阵地,重整阵容,继续作战,而第四师主力,则已移峄县附近。
战报写得很精彩,但改变不了临城陷落的事实。一开始要汤恩伯增援滕县,他说应该先掩护主力在临城集结与日军决战。当滕县被日军占领后,他又说自己孤立无援,放弃了临城。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掩盖不住汤恩伯的责任。
三、李宗仁一份奇怪的电文:
李宗仁的这份电文大致意思是让汤恩伯第85军以一部增援滕县,以主力向北迂回到日军侧后,再与川军相机夹击日军。
《台》文说汤恩伯部根本无法完成迂回任务,川军也无法反击,正是因为李宗仁昏聩胡乱下命令,使滕县失去了最佳救援的时机。
汤恩伯军团战报中的电文
为什么说这份电文奇怪呢?因为在我们披露的史料和对岸公开的档案史料中均未找到电文原始内容,孙震的战报中也未提到相关内容,这份电文只出现在汤恩伯的电报中。从内容上看,很像是日军迂回滕县之前做的一个总体战略部署,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汤恩伯事后写战报的时候搞错了日期。但因为只有一个原始出处,我们无法进行复核。
李宗仁以一个营起家,在北伐中是绝对的主力,其能力是被外界普遍认可的,在明知敌我悬殊的情况下,想必不会出此险招。当然,如果那份电文真的存在且日期没有搞错,那就权当李宗仁真的昏聩无能了吧。
可汤恩伯是怎么处置这份电文的?在电文的下面,汤恩伯接着说
按当时情况激变,敌约一混成旅团越滕县南犯,除我之铁甲车两列在南沙河以南被敌炮毁外,并有敌机械化部队,沿南沙河之东南北王庄一带猛向官桥、临城迂回中。根据上项情况之变化,已无法施行上项命令规定事项,故只能就当前实际情况作适应机宜之处置矣。
看到没有,汤恩伯完全就没管那份电文。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台》文的作者却说汤恩伯还在向邹县迂回,并因此放弃救援滕县。难道他看到了汤恩伯的电文,却没看到紧接着下面一行字?他这不是故意歪曲历史,就是亲自代替汤恩伯去迂回了。
四、汤恩伯是真英雄?
不可否认,汤恩伯军团最终在台儿庄大战中获取了最大战果,但战果得来的前提是川军拼死守藤县,庞炳勋、张自忠拼死守临沂,这也完全在李宗仁的战术安排之中。
对于汤恩伯来说,自从出动以来就在讨价还价、变通执行,最后才跳出来摘桃,而且还是等到桃子熟到快烂了才出来。在台儿庄正面战场,因为汤恩伯“逡巡不前”,31师师长池峰城差点上演了王铭章同样的悲剧。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展开讲还需要一点篇幅。
我们只需要简单看看老蒋4月5日发给汤恩伯的电文:
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分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究竟有无把握,仰即具报为要。
老蒋虽然经常在日记里骂人,但这样直接斥责嫡系高级将领恐怕也是不多见,汤恩伯一直搞变通,阴奉阳违,连老蒋都看不下去了,为什么还有人想替他洗白呢?
汤恩伯确实打过硬仗,南口战役他被吹成英雄,其中恐怕有著名记者范长江一半功劳吧?但不要忘了汤恩伯还有另外一个名声,在河南老百姓眼中有四大害:水旱蝗汤,汤恩伯位列其中。
1944年豫中会战的时候,直接激起河南民变,老百姓伏击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残部,抢夺他们的枪支,连汤恩伯司令部的电台都被抢走了。这些都是汤恩伯长年经营河南的结果。
当然汤恩伯抗战有功不假,说他是英雄也沾点边,如果说他是台儿庄战役中的真“英雄”,那牺牲的王铭章算什么?张自忠、庞炳勋、池峰城等人难道都是假英雄?
对于历史人物,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解读历史一定要符合客观事实,不能曲解,不能为了吹捧某一人而极力抹黑其他人。
2025-02-13 03:55:02
2025-02-13 03:52:46
2025-02-13 03:50:30
2025-02-13 03:48:14
2025-02-13 03:45:58
2025-02-13 03:43:42
2025-02-12 23:16:29
2025-02-12 23:14:14
2025-02-12 23:11:58
2025-02-12 23:09:42
2025-02-12 23:07:25
2025-02-12 23:05:10
2025-02-12 23:02:54
2025-02-12 23:00:36
2025-02-12 22:58:20
2025-02-12 22:56:05
2025-02-11 23:19:56
2025-02-11 23:17:40
2025-02-11 23:15:24
2025-02-11 23:13:08